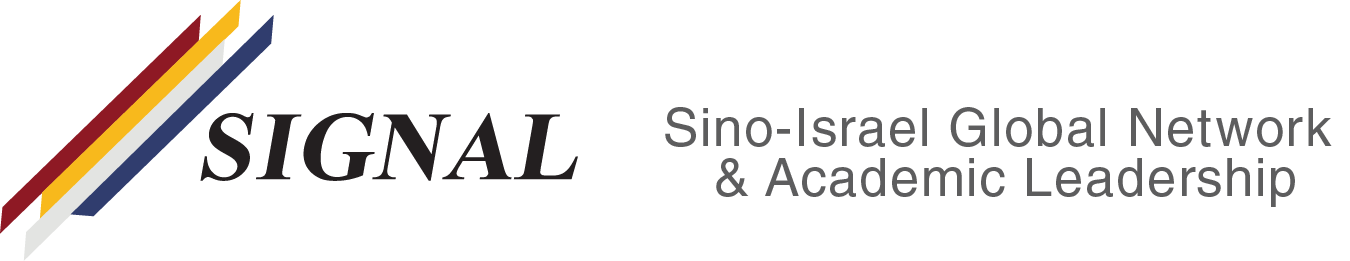作者:内奥米·海德(NAOMI HEAD)*
摘要:同理心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固有成分,这一说法在国际关系(IR)中还没有充分的理论定义。本文从这一前提出发,以世界政治中有关情感的新兴辩论为基础,认为应该通过建立一个跨学科和批判性的框架,来理解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同理心和此类同理心触发的过程,以此进行更为严格的同理心研究。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首先,国际关系中存在同理心,而本文强调了人们对此现象产生的主流观念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特定的社会政治理念适用于特定的社会背景,本文指出此种情况下的同理心可能会衍生出一系列不同的含义。本文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间的冲突为研究对象,确立并阐明了两种替代解释:同理心的使用既是一种非暴力抵抗行为,也是正常化策略。
内奥米·海德(Naomi Head)目前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政治学讲师,教授有关冲突转换、同理心、国际关系和批判理论的课程,并撰写相关文章。她是伯明翰大学冲突,合作与安全研究所(Conflict, Cooperation and Securit)的荣誉研究员,著有《证明暴力行为:科索沃的交往伦理与武力使用》(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不要评判你的邻居,除非你穿着他的鞋走两个月。1
同理心被认为是人类的核心能力,也是政治理论、神经科学、应用语言学、社会心理学和哲学等学科中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尽管同理心已经成为和平研究和化解冲突领域的一个相关概念,并且后者在情感方面的著作不断增多,但同理心在国际社会中依旧不被重视。虽然同理心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但很少有人试图用严格的理论解释同理心在(国际)政治领域是如何运作的。2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把对同理心的注意力集中人际或群体间的层面上,比如同理心的调节功能,同理心在解决问题研讨会中的作用,或同理心在和平建设进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其在不同国家和社会间更广泛的政治作用。然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等人不断在公共场合提到“同理心缺失”的现象3,而其他学者则认为当今正是“同理心时代”的到来。4
由于这些主张有助于对同理心进行描述,且在公共领域有积极影响,因此当前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讨这一概念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提供了的对“同理心”一词的跨学科定义和用法介绍。虽然叙述尚不详尽,但它为发展一个更具批判性的同理心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平台。本文阐述了同理心的主流话语在概念上的一些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往往具有规范性和渐进性的特点。5这些局限包括:缺乏对“同理心政治”的认识;目前的许多辩论都没有充分考察同理心可能在哪些社会政治条件下产生;或者当被行为者采纳时,同理心可能不具政治性质。文献中还缺少对同理心过程的关注,而这一点却极为重要。在这些过程中,通过对包含个人和集体在内的社会的不同层次进行分析,同理心可能得以实现亦或受到限制。将同理心融入最近国际关系中关于叙述和情绪的辩论,这些辩论已经开始理论化情绪如何作为政治行为的激励因素在从个人到团体到国家的政治光谱中运作,这对国际关系学者来说,仍是一大挑战。6长期以来,人们认识到,与冲突的可持续接触需要解决其情感维度的问题,7然而,尽管在这个变革过程中同理心是首要的,却很少有人明确给予很多关注。
这篇文章承认同理心在规范性维度的重要贡献及其在和解过程中的强大作用,但也主张有必要将同理心与其是社会政治背景相结合,主张承认存在权力不对等问题。8 正如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所写,“批判的意图不是要破坏其对象,而是要解释它被认同和被排斥的原因及动力。”9 基于此,本文试图揭示支持主流同理心观点的假设,并通过识别对同理心的其他解读来解决这些问题。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旷日持久的冲突仍然是研究同情心的重要背景,这在国际政治中是最具挑战性的案例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在以同理心为中心的奥斯陆协定(the Oslo Accords)颁布之后,地方和国际组织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交往活动,而这些活动都未能从宏观上改变冲突或防止暴力再次升级。然而,尽管这给许多人带来了不信任和失望,但仍然有许多个人和组织致力于参与那些对同理心和对话进行多样解读的活动,如下所述,它们本身可能是争执和冲突的根源。考虑到同理心的普遍性,理解同理心的作用对于分析冲突及其转化冲突的潜力尤为重要。
在2013-14两年工作期间,我进行了大约20次采访,试图通过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接触来探索同理心产生的动力。我关注的民间社会和基层组织以非暴力方式处理以色列和西岸的冲突10,并与其领导人或志愿者进行了交谈。大多数受访者参与这些和平组织已有很长时间,并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冲突(反映出他们对外来群体的同理心,互相接触和对话活动的看法有所转变)。他们参与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些是曾拒绝暴力的战斗人员,有些是教育者或学生,有些则是和平主义者,失去亲人的人,等等。我试图了解同理心个体的定义、同理心的表现方式和原因(如果表现出来),同理心的对象,以及他们认为在冲突产生及其转变过程中同理心的作用。关注基层行为者既反映了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同理心的特征,即主要是人际或个人过程,也反映了同理心是人与人之间和平交往的主要渠道。11
基于这一研究,本文通过关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方诠释,实证地强调了现有话语的上述局限性,揭示了同理心可能的意义范围;也就是说,同理心被理解为既是一种非暴力抵抗的实践,也是一种正常化的策略。广义地描述同理心反映了批判理论和解决问题理论之间的考克斯( Coxian)差异。用这样的术语来描述同理心的特点,大致反映了考克斯对批判理论和问题解决理论的区分。在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著名框架中,批判理论 “不把制度、社会和权力关系视为理所当然,而是通过关注它们的起源,以及它们如何以及是否可能在变化的过程中,来对它们提出质疑”12。这其中包含一种解放能力,体现在行为者将同理心归结为非暴力抵抗的意义上。反过来说,“解决问题的总目标是通过有效地处理特定的麻烦来源,使这些关系和机构顺利地运作”13。这反映了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 “正常化”做法,即寻求使现有条件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挑战占领的历史条件和不对称性。探讨这些差异并不是要把所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经验都纳入这些解释之中。相反,它试图提请注意在相对较小的访谈样本中明显的模式,以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如何将意义归结为同理心?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同理心,会发现同理心的意义提供了一系列可能的实践和解释。
至少在社会科学中,像情感一样,对同理心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话语分析。行为者(个人和集体)正是通过语言和表征,来赋予行为和认知意义。语言上的联系表达提供了一种手段,以确定琳妮·卡梅隆(Lynne Cameron)所称的 “同理心姿态”14。我认为,如果不参照同理心表达的具体社会政治条件,就不能对同理心的认定进行充分的解释。因此,这是对同理心的解释论而不是因果论。解释个人和集体赋予同理心的含义,是为了帮助理解这些做法如何塑造,以及如何被社会身份和冲突叙事所塑造15。虽然为了论证的目的,重点仍然是将同理心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但这并不是要削弱对同理心与其他各种情感和认知过程密不可分的认识。虽然本文无法公正地说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社会各群体之间和内部的许多分歧,但我并不认为这些对同理心的解释完全代表了任何群体的整体,也无意贬低群体内部的社会动态——包括不同声音对集体叙事的潜在破坏。然而,经验证据中有足够的一致性,表明这些解释与一系列个人和组织产生了共鸣,这些个人和组织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采取了特定的叙述方式,证明了在国际关系中更严格地参与同理心的呼吁是合理的。论证通过以下步骤展开。在围绕这一概念进行定义辩论之前,首先为同理心的理论视角提供一个方向。然后,对在上述的经验背景赋予同理心的意义进行审视。
早期关于实证主义和批评理论的讨论揭示出:要想以某种特定方式传达声音并反映现实,就需要从特殊的角度来看待知识的产生。同理心作为关系性和主体间的认识论条件在实践中揭示了这一点,由于我们探讨存在或其中缺乏相互关联的故事,因此意识到同理心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智力概念。同理心包罗万象,混乱复杂,极具个人性和政治色彩。此外,如果正如我所言,同理心本身包含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可能性,那么在研究同理心的动态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对主体性的构建进行重新思考。对此,奥德-勒文海姆曾写道:”个人不仅仅是社会现实的解释者,而是能够通过对社会制度、实践和现象的思考来了解他自身的人”16。主观性构建超越了狭义个人范畴,这就超越了单纯的个人,将故事置于社会和政治的背景下,将个人的生活和身份与他或她所处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奥德•洛文海姆的这一构想与 C.赖特•米尔斯关于社会学想象力的蓝图极为相似。米尔斯写道,实现这一蓝图须掌握历史、生物学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关系17。在对同理心动态进行重要研究时,把握这一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将身处特定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个人联系起来,还有助于人们理解影响个人同理心和广义同理心在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流动的推动和阻碍因素。
日常生活中关于同理心的问题并完全从神经系统科学、心理学或哲学角度进行解释。这是一种混乱复杂,难以处理的问题。已有人指出同理心的问题会引发对知识创造性问题的关注:人们如何通过展现同理心来表达其意义?听者又是如何对这一意义进行解读的呢?同理心对任意一方而言都并非简明易懂,具有不均衡性、间接促成性和无从比较的特征18。这反映了克里斯汀•西尔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的观点,即认为同理心作为从主观性向新的同理心过渡的边界领域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政治举措19。同理心总是需要关注主体如何定位自己与他们所处的多重身份和冲突来源的关系。这种通过实地研究而进行的面对面交流展示了在将同理心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人际和结构关系都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同时,这也要求对经过深思熟虑后,对同理心的概况做出阐述。这不仅会促使人们与关注同理心相关的意义和主观性如何产生,同时也将涉及影响这些过程的社会、语言学、心理学和政治条件。
同理心一词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尽管有大量的词与其意义和用法相似,但同理心一词的意义并非具有单一性、一致性和连贯性20。在下面的部分,我会挑选出辩论中的常用语句,以此简要表明同理心已在多个学科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绝非详尽无遗,但可以作为一个传达我对同理心如何定义的渠道,同时这也有助于表达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
同理心可被定义为,一种能让我们与他人感同身受,在认识和情感方面换位思考,并理解他人所感、所需、所想的能力。21尽管同情心、同理心22和怜悯心名义上有所差别,但获得别人的感受既是道德意义上的美德,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哲学家等都将其视为和道德相关的概念。2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理心可算作标准道德行为,孕育着人类的发展进步。关于同理心的讨论反映了其在启蒙人文主义中的哲学起源、世界主义和人权的主流范式,有助于推动人们认识到同理心在扩大道德世界边界、促进社会融合、合作、调和以及人性化进程上起到的积极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感他人所感不言自明,且具有普遍适用性。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权利革命表明,实现一种道义上的生活方式,通常需要果断舍弃其本能、文化、宗教以及标准化行为。在权利革命中,道德准则以同理心和理性为原型,以权利的语言加以陈述。24这些理论性争论将参考模式由国家转为个人,并宣称由于同情心含义扩大,因此我们对其他人也负有道德责任。25尽管对同理心的正面解读或许对转变冲突、达成和解具有重要意义,但正如卡罗琳•佩德威尔(Carolyn Pedwell)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正面解读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暗示在除本身的进步性、温和性和文明性之外,同理心还具有一种特定的目的性26 。
需要说明的是,对同理心的论述所隐含的标准品质并不存在本质上的问题,关键是这种有点抽象的、自上而下的、在某些情况下是制度化的27获取同理心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排除了对权力关系的充分承认,而这种权力关系构造了特定的情境和处境的情境。
正如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所言,“世界主义公民权的狭隘概念围绕着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这是权力和财富不对称的残留”。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质疑这种人文主义价值观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将同理心视为如此而非其他,例如,将其作为一种良性的、有益的和解过程,即以特定的方式构建人和国家的身份认同,这种方法蕴含了同情者和被同情者之间等级不对称关系的潜在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同情的语言可能会很“冒昧”;它会通过对他人经历的描述来“剥夺他人的权力”。因此,语言应当用来建立特定的话语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弱者、易受伤害者、贫困者才能从强者那里得到仁慈的同情,或者是如凯西·弗格森(Kathy Ferguson)在和解的文中所说的:“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适当地表达同理心,从而以沉默的形式替代认知、表达和经验【原话】(虽然我不能完全地感同身受但我明白你的感受)。”
这样的话语更有可能将主观思想预先施加给行为承接者,从而提前将叙述具体化,并确定合适的接受同情的对象(或者说是被同情的易受伤害者)。
采用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对此情形积极补救的期望,而且阻止了询问行为接受者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是如何并且为何经历、选择、使用以及理解同理心。这一行为模糊了同理心富有争议的定义,它被接受的原因及动机,其使用的方法以及在发生权利关系时充当的角色,这些相比于其他来说更为有益于:聚集多维度创造“同理心政治学”。
皮德威尔(Pedwell)基于目前的讨论提出问题,他认为,努力培养同理心可能不如检查同情“失败”的潜在原因和影响重要—在失败的情况下,同理心到达了其领界点,遭到其预期接受者的忽略或拒绝,而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或者根本没有意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等级制度下,与其假设同理心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更应该考虑一系列更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同理心?它是做什么的?它为谁服务?它的风险有哪些?
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同理心的研究可以超越其存在于现实主义和自由思想中的对立。许多现实主义者委婉地拒绝同理心相关理论的同时,世界自由主义思潮倾向于让其脱离社会政治背景,并给同理心提供了一种相对单一的表现形式——一种良性的、有益的和道德的过程,使其成为组成政治社区伦理的一个关键要素。这种宏观层面的同情方式通常假设认为无论地点、背景和权力关系如何,同理心的表达、解释和益处都异曲同工。相比之下,我认为同理心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有所不同。以微观方法研究同理心如何“由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构成并在其中发挥作用”。
这种在宏观层面的同理心通常会做出这样的假设,无论地点、背景和权力关系如何,同理心的表达、解释和好处都是一样的。相反,我认为,同理心的意义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是不同的。35微观方法旨在研究同理心如何在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形成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重新)定义同理心
人们普遍认为,同理心是一种存在模式,它将我们与其他人联系起来,促进主体间关系,使个体能够摆脱知识的局限性。37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主体间性是同理心存在论和认识论的前提。事实上,理查德·内德·雷博(Richard Ned Lebow)曾这样写道,同理心反过来会鼓励我们将他人视为与我们同样平等的本体,并认识到与他人建立一种亲密关系有利于自我实现。38 因此,同理心最常见的定义之一是,关注他人的想法和感受,这并不令人惊讶;换句话说就是换位思考。从根本上说,同理心包括,一个人能够把其他人当人看待。而这与阿克塞尔·霍内斯(Axel Honneth)关于在人类交流过程中建立主体间性认知的观点产生了共鸣。39将他人视为本体论的基础等同于拥有同理心,因此,不能或拒绝将他人视为本体论的基础会阻碍同理心的形成。
这种主体间关系的内在潜力象征着一种转化能力。而这种转化必须从家庭教育开始,从自我开始。正如克莱尔·亨明斯(Clare Hemmings)指出的,同理心可以成为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主体将那些令自己舒适的东西转移到其他人那里去,从而欣赏和理解他人。40同理心的主体间性的影响存在于个体主体地位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存在于同理心的形成过程之中,以色列和平学校主任纳瓦·索南夏因(Nava Sonnenschein)指出:深入了解其他人的存在,而不是为了面子工程,也不是为了追究责任,所以不要试图做到完全对等,而应真正关心对方并承担责任,你应该做的是改变现状。41这种转变可以从以色列或美国的犹太人中得到探究,他们自称是自由派或者是温和派,认为以色列安检站等同于机场安全控制站,但却参加了西岸或耶路撒冷北部隔离墙造成的飞地的“马瑟姆观察(Machsom Watch)”行动。42什么样的紧张和可能性可能存在并通过这种挑战现有主观的经验出现?
广义上说,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已经认识到,同理心能够抑制攻击性行为。43在这些学科中,自动同理心和认知同理心也产生了差异。44前者类似于对他人经历的自动情绪反应——情绪传染和情绪识别/反应是常见的替代术语——而后者则要求行动者有意识地产生同理心,指的是代理和认知视角的能力。这种差异也涉及到情绪研究中的一些争论,争论点在于情绪主要是认知的感知还是身体的感知。45
认知同理心促使行为人去理解他人的观点,而不必在情感层面上分享。虽然同情表示关爱或关心他人,但认知同理心可能被用来伤害到另一个行为人,这体现在军事战略的第一条规则中就是:了解你的敌人。根据这些观点,马修·瓦尔德曼( Matthew Waldman)指出,政府所实行的同理心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分析工具,它不需要任何类型的同构或情感分享。46这种形式的同理心还需要能够容忍它可能带来的情感矛盾和道德矛盾。47重要的是,认知和情感之间的区别分析,在目前看来,强调定义同理心的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是同理心的不确定性:在进行调查之前,我们不应该提前设定一种善意或积极的意图。第二,在不同的学科中,认知和情感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得不到重视,而这种差异承认了情感在塑造行动者的动机、意图、判断、推理和信仰中所起的作用。48
因此,同理心被视为是一个跨时间维度运行的主观的、动态的、认知的、情感的过程。它包括对他人观点的认知理解,以及情感分享。49这意味着愿意接受另一个人或群体对事件的理解。即使一个人只是对另一个人拥有认知同理心,他也不能把他们的认知过程和他们自己的情绪分离开来,这决定了他们如何处理接收到的信息。同理心总是需要个体的认知-情感过程,而集体同理心指的是对他人的认可和合法化的集体叙述,并捕捉个人和群体之间在信仰、身份、情感取向和叙述方面的复杂关系。
卡梅隆的同理心话语动态模型界定了一系列阶段,在概念探索和实证研究方面提出从时间维度入手。该模型提出以下四个阶段:(1)同理心的背景条件(参与者在对话时具备的一切要素,包括会话的程序准备、个人/群体的态度、信念或生物性情);(2) 对话中出现的同理心局部话语动态(以分钟为时间线);(3)对话中出现的同理心语篇模式(以分钟或小时为时间线);(4)在公共领域、政治或社会话语中出现的跨日/周/月/年的稳定性同理心。在各种人文交流中可以确定第二和第三阶段,但当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社会的精英话语或公众舆论缺乏第四阶段—稳定性同理心,这导致人际或群体间对话的实效性和目的性存在一些冲突 (下文讨论)。一位参与中东和平研究(PRIME) 双重叙事项目—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为例的教师阐述了时间对同理心过程的重要性,他说:”当看到对方的叙述时,起先我感到愤怒和沮丧,因为其与我方的叙述差别极大。我觉得对方的叙述没有基于事实,是编造的。后来,我学会在认知上接受这种差异,但还是觉得我方叙述比对方的更可信。直到最近,我才理解对方叙事背后的逻辑,甚至在情感上对他们的经历感同身受。假设这个过程花了我四年时间,想象一下,如果是学生或是他们的父母,该花多少时间去理解?51
这清楚地表明,同理心的生成需要时间,而缺乏这种时间会阻碍关系的可持续转变。这些很可能是在长时间内与不同的参与者一起发生的迭代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转变成为可能。52在此思路下—以及批判理论的传统—我认为,同理心的动态过程总是包含着转变自我和自我-他人关系的内在潜力。正如伊夫塔赫·罗恩( Yiftach Ron) 和 伊法特·莫阿兹(Ifat Maoz) 所说,“正视政治与族群冲突中有争议的事件…是群际互动的一种变革形式,因为它可以为自我和他人不同情感和道德关系之间创造空间。”53然而,重要的是,这种变化不是必然的,也不起决定性作用; 在特定的时刻,参与者在对话中决定要表达同理心,之后并不一定会以特定方式行动。他们正在进行的行动将涉及物质利益和概念因素,成为这一复杂过程的一部分,这些因素或促成、或限制特定的结果。在决定表达同理心之后参与者会采取某些行动,正是这些行动揭示了参与者想以某种方式为他人谋福祉。这需要通过反复互动逐步建立起来。正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参与者所表示的那样,“你必须促成这种变化…因为现实非常强大,可以抹去这种影响。这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须通过后天培养。你可以有同理心,却什么都不做。54
面对棘手的冲突,矛盾双方往往为己方和对方建立单一身份,并以此为目的通过历史叙事来加强这种身份。这种身份和叙事几乎在不遗余力地揭示对方的弱点,影响(并掩盖)了接受对方叙事和身份的能力。虽然揭示对方弱点对于个人和群体的转变仍很重要,但这关系到一个更大的转变,正如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我们不单单依赖于单一的、离散的接受准则,更依赖于历史上阐述并实施过、更普遍的‘可接受性 ’条件。55“这些政治和历史上的偶然条件影响了接受特定构成主体的可能性,以及接受的不对称性。因此,对同理心及其促成/限制条件的关注使我们要问:现有的准则[叙事和结构]如何指定接受度,56这对维持或转变冲突有什么影响?因此,在不对称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责任而不是通过简单的相互作用来塑造主体间的动态。纳瓦·索南夏因(Nava Sonnenschein)回应了这一论点,她指出,以色列犹太人必须转变:”在他们谈论占领者的时候,即使你来自特拉维夫,即使你不在那里服役,你不能认为这与你无关,你必须真正承担起责任,你属于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正在对其他人造成影响。你要承认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57 鉴于争取认可是冲突的核心,特别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社会内部不对称的结构和关系中所反映出来的那样,责任与相互作用问题与政治同理心高度相关。
同理心作为非暴力抵抗
虽然非暴力的含义和范围很广,也有争议,但非暴力的说法在这场冲突中得到了有力的阐述。此外,作为非暴力抵抗的一种形式,同情心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明确表明的一种战略。59这与此前的同理心定义相吻合,该定义强调认知和情感紧密相连,注意到在决定同理心并采取相应行动时所涉及的中介,突出了对旷日持久的冲突局势至关重要的时间维度。它还为同理心的渐进性和良性语篇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将同理心视为一种抵抗形式,打破了 “同情者”(强者)和 “受害者”(弱者)的传统分类。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而言,许多深陷于同理心过程中的人本身也经历过苦难。正如Pedwell所言,”‘选择’同理心或怜悯,其本身就能成为一种维护权力的方式。60选择同理心(而不是以其他方式应对冲突)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政治选择。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积极拥有同理心的是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不仅仅是强者),这种观念把中介归给了那些在传统政治术语中可能被认为是弱者的人。
尽管政治权力明显不对称,但介于巴勒斯坦人之间、以色列人之间、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以色列人之间以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使任何简单的假设和 “谁 “在进行共鸣和 “与谁 “进行共鸣都是不成立的。必须指出的是,在许多团体间对话中,相遇的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关系的不对称性与以色列内部少数群体的声音所表现出的不对称性不同,对于他们来说,共鸣接触可能也代表了一种抵抗占领的形式和自我转变的过程。61当行为者选择同情那些(地缘政治上)处于特权地位的人时,可以将其概念化为一种对压迫制度和结构的反抗形式。团体和个人之间的接触可能产生新的政治可能性和话语。菲利普·哈默克(Phillip L. Hammack)也认为,对于处于难解冲突中的群体来说,接触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变革性—甚至是颠覆性的活动”,因为它提供了一个 “培养抵抗和否定,从维持对抗中获益的社会秩序场所”。66我认为这种抵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出来。
许多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占据主导地位的叙述都以高度两极化的方式来定义“他者”。63通过向对方展示你是一个有经验、有情感和有信仰的个体来反击,这是一种抵抗形式,因为它拒绝接受以色列占领这种不人道功能; 相反,它重申并赋予人类品格以韧性。64它还可以在认知、理解和分享经验的过程中,使自我和他人的转变成为可能。这不应与正常化相混淆,也不意味着任何一方应放弃自己的权利或要求。65然而,怀有同情并没有改变以色列依然占领着巴勒斯坦领土的这一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权力不对称的条件下,同理心的价值和动机不在于在民族群体之间建立桥梁和共同理解,更多的是自我的建构和定位。鉴于此,可以说,采用特定的身份和叙事(并抵制他人)有助于确保自我意识。
利用同理心拒绝接受因占领产生的不平等,同时助长个人身份、机会、情感和信仰,使个人不太可能通过报复他人而让暴力继续循环。巴勒斯坦“和平战士”组织共同创始人巴萨姆.阿拉明(Bassam Aramin)表示,采取非暴力对巴勒斯坦人有好处,因为这可以改变巴勒斯坦人在他人心目中的暴力形象。66阿依达(Aida)难民营中阿尔洛瓦德(Alrowwad)的负责人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布让(Abdelfattah Abusrour)认为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运用同理心有助于“美丽自我”的建立,它关注的是在不平等条件下人类将会怎样;它滋养创造力和道德想象力;它创造坚韧性以抵抗冲突中灭绝人性的因素;它要求我们反思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通过对人类本身的关注,它超越了继续占领的政治合理性。67回顾我们对权力关系的关注,伯利恒的Wi’am中心主管周彼(Zoughbi Zoughbi) 明确表示,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庇护或同情的因素;同理心可描述为平等公民之间的关系,行为者在自我转变过程以及特定政治环境中自我和他人存在与发展的关系中承担责任。68这些方法在一些拥护非暴力的基层组织中显而易见,这些组织往往注重通过艺术、音乐、戏剧、领导力、群体内对话和教育、调解、非暴力培训、讲习班和媒体参与等形式进行教育和自我发展。68
基于这种个人对转变的责任感,同理心还提供了关于冲突的重要教育来源,它能促进第三种说法,即承认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历史,承认犹太人大屠杀和巴勒斯坦灾难日。卡琳·菲尔克(Karin Fierke)认为,有必要创造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双方“能认识到他人的行为如何受到自身痛苦经历的制约”。70这可以使双方意识到他们为彼此带来的痛苦,并打破对自己“受害者”这种身份的绝对信念。71例如,马瑟姆观察、Tiyul Rihla、Wi’am中心等组织提供的教育(文化、历史、政治)旅游,以及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国际游客提供的“打破沉默”(等等)。换句话说,同理心可以促成认知失调。72 我认为,这可能是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建设性手段。 莱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两种要素在心理上不一致时,它会为个体解决这种不一致创造一种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同理心提供了一种动力,通过承认自我和他人的痛苦来减少心理(和物质)冲突。
当代关于巴以冲突的主要叙述大多围绕着犹太人大屠杀和巴勒斯坦灾难日这两个关键的历史事件,但又绝对不限于此。这些事件本身及公众的对其描述都折射出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早期对于犹太国家的定义和争论起了冲突,而通过回忆大屠杀和大流亡期间所经历的创伤,以及这些记忆在当代的(重新)表述,这些冲突又得以延续和加强。直到19世纪60年代,大屠杀才成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的中心,但自那以后,它便融于以色列人民的集体记忆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使人们感受到生存威胁和不安。 这两段复杂多变的历史都是当代政治的合法化和正当化叙述,并形成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社会的政治争论的因素73。对冲突双方的许多人而言,他们都不会承认另一方所叙述的历史,双方的集体创伤都因此加强,从而限制了他们对多种叙事方式感知的能力。74正如巴特勒(Butler)所言,“公共领域是由可记载的东西构成的,而对出版的监管决定了挑选什么内容作为现实,也决定了如何报道人的生死”。75这又将我们拉回到承认或否认个人和集体叙事的行为,以及这些决定对巴以冲突双方带来的不对称后果。因此,聆听并表述“不可说的”内容,即经常为社会和政治规范边缘化的 “他者”的叙述,可以被视为一种非暴力抵抗行为,因为它引发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围绕着相互承认和承认他者、履行责任、克服弱点以及循环出现集体创伤和暴力模式。76正如一位巴勒斯坦人所解释的那样,“我们必须向以色列犹太儿童讲授巴勒斯坦灾难日事件,向巴勒斯坦儿童讲授犹太人大屠杀事件77”。
中东和平研究所(PRIME)采用的双重叙事方法就是一项例证,该方法在2002年至2009年期间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教师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编写并教授由两种平行叙事方式所构成的历史课本,讲述上世纪在两国发生的事件。该项目旨在启动一项进程,使“两个民族,特别是年轻一代,能够超越对本民族叙事的单维认同”78,因为这种单维认同会使得冲突永远都合理存在。通过多次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举行会议,该项目七年的时间框架反映了这样一种认识,即“适应双重叙事方法需要长期的教授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79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出于不同的原因,认为双重叙事方法是一种政治威胁,对那些希望将双重叙事方法引入课堂的教师设置了重重障碍,这说明通过叙事表达和同理心这种复杂过程所进行的教育可以作为一种抵抗形式。80当局明令禁止在课堂上讲授这种材料,表明重新制定教育方法以及更广泛的政治争论方面,面临着来自社会和政治的多重阻碍。对此,一些教师选择在家中授课,教授学生正规课程外的东西,这就表明了他们非常重视这种叙事教育形式。
在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情况下,上述形式的同理心与对不公正的认识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存在。意识到这种紧张关系,就可以摒弃这样的说法,即在这种情况下,同理心仅仅是希望通过与“他人”的人际交往建立桥梁或超越差异。然而,同理心是不断变化的,是具有局限性的。也就是说处于边缘化政治(文化和经济)地位的人可能会把同理心当做战略一部分,从而抵抗侵略及泯灭人性的后果。这种同理心因为更关注被侵略的人们,从而促进了解放的可能性。
同理心常态化
不对称权力关系的存在不仅将同理心概念化为一种反抗行为。重要的是,一些巴勒斯坦人已经形成了这种认识,即同理心可能构成了一种常态化的策略,进入了派德维尔(Pedwell)称之为“同理心失败”的境况。81这为同理心与政治有关这一观点提供了事实基础,也为这样一种观点提供了根据,即支撑有关同理心的许多论述的有益假设必然受到质疑。基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现状,常态化是一个充满政治意义的词。巴勒斯坦学术和文化抵制以色列运动(PACBI)将“常态”定义为:在巴勒斯坦或国际上参加任何项目、倡议或活动,其目的是(默示或明示)使巴勒斯坦人(和/或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人民或机构)走到一起,而不把抵抗和揭露以色列的占领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压迫作为其目标。82
此外,巴勒斯坦学术和文化抵制以色列运动(PACBI)表示:“这有助于人们将常态化当作“思想殖民”,即被压迫的主体开始相信,压迫者面临的的现实是唯一必须接受的 “正常 ”现实,而压迫是必须面对的生活事实。83这与 “物化”的概念有相似之处:这个词最早由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提出,并被其他批判理论家所采用,以审视人为现象的自然性,不可避免性和客观性,质问人类对待彼此的手段。
在PACBI所定义的正常化语境中,对话结果(通常包括同感因素)往往成为特别关注对象:“对话”、“疗伤”和 “和解”的过程,如果不积极地以结束压迫为目的,无论其背后的意图是什么,都会给予压迫性的共存特权,而以共同抵抗为代价,因为它们在实现正义之前就假定了共存的可能性。84这种异议大多产生于那些以人际交往或社会心理学家所熟知的接触假说为基础的活动中。接触假说是由戈登·阿勒波特(Gordon Allport)提出的,85其观点是:“冲突中的人们只需要一个机会来相互了解,一旦了解之后,个人很快就会发现,在群体身份(如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的外衣之下,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共同身份,即人的身份”。86即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有着正向的人际交流,这种态度是否可能超出对话中的个人,从而消除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相互间通常存在的偏见?但即使是这样,当个人返回到可能无法接受这些观念转变的群体时后,这些积极的变化可能会持续下去吗?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研究者强调,观念转变之后恢复“正常”生活,“重返”问题是这些努力未能带来持久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关键原因。87
虽然同理心是这些面对面接触的核心成分,但它们缺少两个因素,从而招致人们对常态化的批评。这些是在各党派中享有平等地位和使社会身份发挥的作用受到认可的要求。88当一场冲突使得各方处于(例如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不对称地位时,很可能会加剧而不是减少现有的不平等和偏见。89正如艾瑞尔·阿德勒(Arie Nadler)所写,我们不能要求个人“把象征自己社会归属和社会身份长袍留在房间外面”。90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他们在不了解自己的归属感、历史和身份的情况下,进行一种非政治性的共情。这不仅在心理上要求太高,91而且没有考虑到导致参与者不对称体验的政治因素。用巴特勒的话说,这些政治上和物质上的不对称导致了认可不同,从而形成了对同理心的角色和目的的不同解释。
这种基于接触的对话干预的期望通常以互惠为核心。然而,达莎·杜哈切克(Dasa Duhaček)和亨明斯明确表明, 关于为什么这可能是不可能的或不可取的,有历史和政治原因,即:“位置和感知的不可通约性很可能破坏主体的能力[或意愿],通过感觉作为/对于另一个主体来改变自己。” 92
和平学校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阿拉伯-犹太人的对话和接触,拉姆齐·苏莱曼(Ramiz Suleiman)根据和平学校的经验提出了一个与缺乏平等地位的后果有关的重要问题。他指出,在以色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接触中,巴勒斯坦与会者经常寻求将互动转移到群体之间,以提出具有政治和集体性质的问题,重点关注以色列国家实行的歧视。相反,犹太参与者倾向于将互动转移到人际层面,从而促使关系正常化。这是权力关系差异的直接结果,并助长了每个群体的冲突导向行为模式。93
这符合并解释了一些巴勒斯坦人在接受采访时所阐述的观点,即在占领继续的情况下,小组间对话和建设和平工作不可能取得成功。94有人认为,这种努力有助于分散对占领现实的注意,并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维持现状有助于保护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因此,人们认为,这些活动有效地维持了现有的权力和地位的不对称,同时确保以色列在参与这些活动时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建设性态度。95 “同理心”、“对话”和“建设和平”条款—以及纳入国际和平建设的策略—见证了许多人幻想的破灭。他们认为这些策略是破坏性的,就像是他们在教授一门语言,学生不仅不是同一种群的人,而且脱离了特定的安全框架,该语言就无法改变或反映学生们面临的日常政治现实。在有利的工作场所中,通过对话以及其他和解手段达成的共情,会令人产生一种平等的幻觉。96而当巴勒斯坦人下班回家,通过检查站并遭受以色列人侵略的不公正待遇时,就会明白在日常生活中,所谓的平等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情况的后果是,当脱离可持续政治变革的框架时,这些推动力就会使参与者们产生疏远、困惑和认同障碍。卡茨和卡哈诺夫支持同理心可以促进正常化这一观点。他们表示,“据政治模式(互动模式)的支持者表示,心理模式是有操控性的。97由于不关注权力不对称这一问题,这种模式也有使个人和更广泛的冲突解决方法去政治化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以增加同理心和减少群体间敌意为导向的干预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会增加对外部群体的负面情绪和群体之间的不信任程度。98与将同理心构建为一种非暴力抵抗形式不同,这种对同理心的批判则表明,同理心会导致认知失调,这对个人和他们所属群体都无益处。在此背景下,通过加强群体内部认同和采取反抗压迫的替代策略,可能会解决认知失调问题。同理心的意义再一次与冲突的叙述手法和相关的身份概念紧密相连。
总结
将生活经验中的同理心视为一个易变的伦理政治策略,这响应了这里所提出的一个呼吁,即对同理心采取更严格、更具批判性的态度。将同理心解释为一种非暴力抵抗和常态化的策略,有助于探索同理心作用的意义产生。以这种方式构建同理心,就表示它不会是良性或有益的,并且能让我们认识到同理心不可避免的政治和情境特征,以及通过跨学科研究以充分解释同理心的动态之需要。这包括但不限于在社会和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和平研究和叙事研究等领域的最新发展。
虽然同理心可视为寻求认可的一部分,且其缺失是社会和心理伤害的又一形式,因而其正常化进程难以避免,但是也必须承认,同理心作为一组生活实践,它与这一正常化视角既联系,又偏离。因此,伊朗呼吁对同理心采取更严厉的批评方法,源自于这样一种认知,即要证明同理心可以作为终结冲突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弥合群体之间的差异并调和过去的创伤时,单靠受访者提供的故事和经历不够的。对同理心的批判性做法(至少)包括以下核心问题。首先,要规范性认知和探讨同理心的变革问题,例如,它是否是一种非暴力抵抗或协商性战略。第二,它应该与社会结构、社会话语以及社会制度相融合,这使得同理心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但同时也限制了其他形式的同理心,从而维持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批评者将探索并力求将生活经验中的同理心以及在特定背景下行为者长期以来赋予同理心的各种含义概念化。表达同理心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层面,为激发特定形式的互动目的和意图预留空间,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人们对关怀的假定善意或同理心所带来进步的后顾担忧。因此,它并未回避同理心的服务对象及目的。
第三,它能解决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跨越多个分析层次的同理心问题。一个关键推论就是探究同理心产生的方式、地点、时间、原因,传播方式以及由谁来传播、往复或阻断,这些过程和行为的灵活度,它们与国际关系中广义情感之间的联系,以及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的普遍联系。这些问题对解决和反思当前国际仲裁、建立和平和冲突转换方法产生了很多影响。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理心、建立和平和对话项目常常被视为问题所在,而非解决办法。同理心与正常化政治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就解释了这一问题。尽管这些过程可能转变个人观念,但它们‘似乎对整个社会的规范、制度和公共领域的地位没有太大影响’。99目前,对这些过程的理论性或经验性解释仍然较少,这可能导致或阻碍个人和人际层面向社会政治结构的同理心过程转移。
尽管个体对于同理心的培养或阻碍至关重要,但个体深深融于其人脉圈和信仰之中,这些人脉和信仰有助于他们转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并将这种转变用于社会和政治变革。同一性与对冲突的集体叙述密切相关,集体叙述同样也是影响同理心方法的一个构成因素。阿萨夫·西尼弗(Asaf Siniver)主张要认识到“集体身份和敌对形象在历史冲突中的重要性”,“识别这些心理障碍并克服它们是成功解决冲突的关键”。 100这种遍布巴以冲突的集体和历史性叙述反映了特定社会和情感信仰,包括对安全、“敌对”势力、自我和平形象、欺骗以及自身目标公正性的看法,它们为特定的政治公正服务,并助长了暴力和冲突的恶性循环。101这种叙述能阻止在公众论述和精英领导层面上民族社区之间的同理心制度化,从而削弱基层群众和市民社会同理心接触的影响。
翻译:中国国际能源舆情研究中心 韩月萌,马甜甜,董帅,王梦雨,杨璐,杨奕,张君,何佼阳,白文姣,李紫荆,王海苗,杨英娟,杨伟伟,马洪玲,马佳静
审校:关媛
* Thanks must go to the anonymous RIS referees for their discerning and constructive comments.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Adam Smith Research Foundation at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and the Carnegie Trust for the Universities of Scotland for the funding that supported the research in Israel and Palestine. My thanks toall interviewees who shared their narratives, thoughts, and experiences with me and to the Kenyon Institute in Jerusalem. Thanks to those who have providedcomments on various drafts of this article: Katherine Allison, Marcus Holmes, Cian O’Driscoll, Ty Solomon, David Traven, Nick Wheeler, and participants atHINT sessions and the Sussex Research in Progress seminar.
1 Cheyenne Native American proverb.
2 Exceptions include Christine Sylvester, ‘Empathetic cooperation: a feminist method for I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3 (1994), pp. 315–34;Michael Morrell, Empathy and Democracy:
Feeling, Thinking and Deliberation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Naomi
Head, ‘Transforming conflict: Trust, empathy and dialog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17:2 (2012), pp. 33–55; Lynne Cameron, ‘A dynamic model ofempathy and dyspathy’, Living with Uncer- tainty Working Paper No. 6 (May 2013); Giandomenico Picco and Gabrielle Rifkind, The Fog of Peace: The Human Face of Conflict Resolution (London: I. B. Tauris, 2014); Carolyn Pedwell, Affective Relations: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s of Empath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Neta C. 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s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4(2000), pp. 116–56; Grant Marlier and Neta C. Crawford, ‘Incomplete and imperfect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empathy and altruism i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doctrine’,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5 (2013), pp. 397–422.
3 Senator Barack Obama, ‘Obama Challenges Grads to Cultivate Empath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northwestern.edu/newscenter/stories/2006/06/barack.html} accessed 30
May 2014; President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in Addres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21 Septem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
2011/09/21/remarks-president-obama-address-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accessed 30 May 2014.
4 Frans De Waal, The Age of Empathy: Nature’s Lessons for a Kinder Society (London: Souvenir Press,
2010); Jeremy Rifkin, 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 The Race to Global Consciousness in a World in Crisis
(London: Penguin, 2009); Roman Krznaric, Empathy: A Handbook for Revolution (London: Rider, 2014).
5 See Pedwell’s critique of empathy in Carolyn Pedwell, ‘Affect at the margins: Alternative empathies in
‘A Small Place’,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8 (2013), pp. 18–26.
6 Brent E. Sasley, ‘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3 (2011), pp. 452–76; Brent J. Steele,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elf-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 (Abingdon: Routledge, 2008); Emma Hutchison and Roland Bleiker, ‘Theorizing emotion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Theory, 6:3 (2014), pp. 491–514; Jonathan Mercer, ‘Feeling like a state: Social emotion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Theory, 6:3 (2014), pp. 515–35.
7 Herbert Kelman, ‘Transform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er enemies: a socio-psychological analysis’, in Robert Rothstein (ed.), After the Peace: Resistance andReconciliation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9), pp. 193–205; Picco and Rifkind, The Fog of Peace
8 This builds on critical approaches articulated in the writings of Sara Ahm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Lauren Berlant (ed.), Compassion: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an Emo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4); Carolyn Pedwell, ‘Affective (self-) transforma- tions:Empathy, neolib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eminist Theory, 13:2 (2012), pp. 163–79; Pedwell, ‘Affect at the margins’; Sylvester, ‘Empatheticcooperation’.
9 Berlant, Compassion, p. 5.
10 While engaging in these debates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article, I recognise that the definition of non- violence is contested.
11 This is not to exclude the role of elite rhetoric and leadership or public opinion from the study of empathy. However, given the focus here is on civil societyand popular narratives of the conflict, this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article.
12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O. Keohane (eds),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08.
13 Ibid.
14 Cameron, ‘A dynamic model’.
15 Roxanne Lynn Doty, Imperial Encounter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4.
16 Oded Löwenheim, ‘The ‘I’ in IR: an autoethnographic accou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6:4 (2010), p. 1025.
17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
18 Pedwell, ‘Affective (self-) transformations’, p. 175.
19 Sylvester, ‘Empathetic cooperation’, p. 326.
20 See, for example, Nancy Eisenberg and Janet Strayer (eds), Empathy and its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 Daniel Batson andNadia Y. Ahmad, ‘Using empathy to improve intergroup attitudes and relations’,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3:1 (2009), pp. 141–77.
21 Rafael Moses, ‘Empathy and dis-empathy in political conflict’, Political Psychology, 6:1 (1985), p. 135.
22 Martha Nussbaum,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39; Steven Pinker, The BetterAngels of Our Natur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2), p. 692–97; Richard Ashby Wilson and Richard D. Brown, Humanitarianism and Suffering: The
Mobilization of Empat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
23 Adam Smith, A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vol. 1 of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 pondence of Adam Smith, eds D. D. Raphael and A. L.Macfi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2 [orig. pub. 1759]);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London: Dent, 1911); Martha Nussbaum, Joshua Cohen (eds), For Love of Country? (Boston: Beacon Press, 2002 [orig. pub. 1996]); Nussbaum, Upheavals of Thought, pp. 335–7; Jean-Jacques Rousseau, Discourses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New York: Dover, 2004 [orig. pub. 1754]); Elizabeth Porter, ‘Can politics practice compassion?’, Hypatia, 21:4
(2006), pp. 96–123; De Waal, The Age of Empathy; Rifkin, 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 Ute Frevert, Emotions in History: Lost and Found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Krznaric, Empathy; Pinker, Better Angels, pp. 210–21, p. 711; William Reddy,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self and emotions’, Emotion Review, 1:4 (2009), pp. 307–8.
24 Pinker, Better Angels, p. 573.
25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 206; Linklater, The Problem of Harm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6 Pedwell, ‘Affect at the margins’, p. 19; Pinker, Better Angels, pp. 711–13.
27 Marlier and Crawford, ‘Incomplete and imperfect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empathy’. Marlier and Crawford acknowledge that empathy, when poorlyundertaken, can lead to paternalistic interventions and programmes (pp. 399–400).
28 Linklater, Transformation, p. 206.
29 Pedwell, ‘Affective (self-) transformations’, p. 165; Krznaric, Empathy, pp. 91–2; Author interview with
Lucy Nusseibeh, Director of Middle East Nonviolence and Democracy (MEND), 13 May 2014.
30 Author interview with Lucy Nusseibeh.
31 Cited in Sylvester, ‘Empathetic cooperation’, p. 326.
32 Pedwell, ‘Affect at the margins’, p. 19; Liisa Malkki, ‘Speechless emissaries: Refugees, humanitarianism and dehistoriciz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11:3 (1996),pp. 377–404.
33 Pedwell, ‘Affect at the margins’, p. 25.
34 Exceptions include Ralph K. White, Fearful Warriors: A Psychological Profile of U.S. – Soviet Relations (US: Macmillan, 1984). See Neta C. Crawford, ‘Humannature and world politics: Rethinking “M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2 (2009), pp. 271–88; Ken Booth and Nicholas J.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Fear, 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8).
35 Andrew Linklater, ‘Anger and world politics: How collective emotions shift over time’, International Theory, 6:3 (2014), pp. 574–78.
36 Hutchison and Bleiker, ‘Theorizing emotions’, p. 498.
37 Clare Hemmings, Why Stories Matter: The Political Grammar of Feminist The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99.
38 Richard Ned Lebow, ‘Reason, emotion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2:3 (2005), p. 42.
39 Martin Jay in Axel Honneth, Reification: A New Look at an Old Idea, ed. Martin Ja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8.
40 Hemmings, Why Stories Matter, p. 201.
41 Author interview with Nava Sonnenschein, Director of Neve Shalom – Wahat al-Salam (School for Peace), 4 May 2014
42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MachsomWatch tour, May 2014. MachsomWatch is a volunteer organisation of Israeli women who oppose the Occupation. They conduct arange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daily monitoring of the checkpoints and tours in the West Bank and Jerusalem area for Israelis and foreigners.
43 Moses, ‘Empathy and dis-empathy’; Jean Decety (ed.), Empathy: From Bench to Bedsid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12).
44 Jean Decety and William Ickes (eds), The Social Neuroscience of Empath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9); Cameron, ‘A dynamic model’; Krznaric, Empathy.
45 Andrew A. G. Ross, Mixed Emotions: Beyond Fear and Hatred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Renee Jeffrey, ‘Reason, emotion, and the problem of world poverty: Moral sentimen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eth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3:1 (2011), pp. 143–78; Rose
McDermott, ‘The body doesn’t lie: a somat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emotion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6:3 (2014), pp. 557–62; Jonathan Mercer,‘Emotional belief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4 (2010), pp. 1–31; 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London: Vintage Books, 1994).
46 Matthew Waldman, ‘Strategic empathy: the Afghanistan intervention shows why the U.S. must empa- thize with its adversaries’, Washington, DC: Report forNew America Foundation (April 2014).
47 Jodi Halpern and Harvey M. Weinstein, ‘Rehumanizing the other: Empathy and reconciliation’, Human
Rights Quarterly, 26 (2004), pp. 561–83.
48 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Mercer, ‘Emotional beliefs’; Head, ‘Transforming conflict’; Morrell, Empathy and Democracy; Jeffrey, ‘Reason, emotion,and the problem of world poverty’; Forum on 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6:3 (2014); Nussbaum, Upheavals of Thought.
49 Cameron, ‘A dynamic model’; Head, ‘Transforming conflict’, pp. 39–40.
50 Cameron, ‘A dynamic model’, pp. 9–10.
51 Sami Adwan, Daniel Bar-On, and Eyal Naveh (eds), Side by Side: Parallel Histories of Israel-Palestine
(PRIME, New York: New Press, 2012), p. xiv.
52 Head, ‘Transforming conflict’, pp. 39-41.
53 Yiftach Ron and Ifat Maoz, ‘Dangerous stories: Encountering narratives of the other in the Israeli- Palestinian conflict’,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19:3 (2013), p. 292,
emphasis added.
54 Author interview with Nava Sonnenschein; expressed similarly in author interview with Zoughbi
Zoughbi, Director of the Wi’am Center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5 May 2014.
55 Judith Butler,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Verso, 2009), p. 5.
56 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Verso, 2004), p. 6.
57 Author interview with Nava onnenschein.
58 Bruneau and Saxe have suggested that ‘“perspective-giving” would be well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members of disempowered and non-dominant groups, whereas “perspective-taking” would be better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dominant group members’ (p. 856), in Emile G. Bruneau and Rebecca Saxe, ‘The
power of being heard: the benefits of ‘perspective-giving’ in the context of intergroup conflic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4 (2012), pp. 855–6.
59 This was a perspective which a number of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practitioners self-identified with in interviews.
60 Pedwell, ‘Affect at the margins’, p. 19; Paolo Freire, 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trans. Myra
Bergman Ramos (London: Continuum, 2000 [orig. pub. 1970]).
61 The same applies to Palestinians and Israelis occupying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positions within their societies.
62 Philip L. Hammack, Narrative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You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59–60.
63 See ibid.; Asaf Siniver, ‘Israeli ident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threat: a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ation’, Ethnopolitics, 11:1 (2012), pp. 24–42; Tony Klug, ‘Israel/Palestine: Trapped by our own narratives?’, Open Democracy (22 December 2013).
64 Author interview with Palestinian NGO leader, 5 September 2013.
65 Author interview with Abdelfattah Abusrour, director of Alrowwad, Aida refugee camp, 5 September
2013. While some groups may continue with intergroup dialogue others currently focus on intra-group dialogue. This depends in part on howindividual/organisational positions intersect with the narrative of normalisation.
66 Author interview with Bassam Aramin, 4 September 2013; Interview with Lucy Nusseibeh, 13 May 2014.
67 Author interview with Abdelfattah busrour.
68 Author interview with Zoughbi Zoughbi.
69 For example, see activities run by Holy Land Trust, MEND, Wi’am Center, Combatants for Peace, CARE, MachsomWatch.
70 K. M. Fierke, Diplomatic Interventions: Conflict and Change in a Globalising Worl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148.
71 Fierke, Diplomatic Interventions, p. 145.
72 Leon Festinger,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57).
73 Siniver, ‘Israeli Identities’, pp. 32–4.
74 See Adwan et al., Side by Side.
75 Butler, Precarious Life, pp. xx–xxi.
76 Examples of this might include: the Israeli organisation Zochrot, the PRIME initiative, and intergroup encounters which address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issues.
77 Interview with Bassam Aramin, Combatants for Peace, 4 September 2013.
78 Adwan et al., Side by Side, p. x.
79 Ibid. p. xiv.
80 Author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Eyal Naveh, Tel Aviv University, 20 May 2014; Author interview with
Palestinian educator, 2 September 2013.
81 Pedwell, ‘Affect at the margins’, p. 25.
82 See{www.http://pacbi.org/etemplate.php?id=1749} accessed 30 May 2014.
83 Ibid.
84 Ibid.
85 Gordon Allport,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54).
86 Arie Nadler, ‘Intergroup conflict and its reduction: a soci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 Rabah Halabi
(ed.),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Identities in Dialogue: The School for Peace Approach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3.
87 Michael Zak, Rabah Halabi, and Wafa’a Zriek-Srour, ‘The courage to face a complex reality: Encounters for youth’, in Halabi (ed.), Israeli andPalestinian Identities in Dialogue, p. 113; Adwan et al., Side by Side, p. xvi; Hélène Pfeil,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Israeli-Palestinian grassroots dialogue workshops: the contribution of a Habermasian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December 2013); Hammack, Narratives and thePolitics of Identity; author interviews with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activists, September 2013, May 2014.
88 Allport recognised the importance of equal status between the parties during contact along with other criteria. This condition has not adequately addressed thebroader asymmetrical relations of power which have framed contact encounters in this conflict.
89 Nadler, ‘Intergroup conflict’, pp. 25–6; Nadim N. Rouhana, ‘Group identity and power asymmetry in reconciliation processes: the Israeli-Palestinain case’,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19:3 (2004), pp. 33–52;
Jonathan Kuttab and Edy Kaufman, ‘An exchange on dialogu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7:2 (1988), pp. 84–108.
90 Nadler, ‘Intergroup conflict’, p. 6.
91 Hammack, Narrative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 14.
92 Hemmings, Why Stories matter, p. 204.
93 Ramzi Suleiman, ‘Jewish-Palestinian relations in Israel’, in Halabi (ed.),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Identities in Dialogue.
94 Author interview with Abdelfattah Abusrour; author interview with member of East Jerusalem NGO,
6 September 2013. The interviewee’s views were based on prior experience of and participation in dialogue and peacebuilding projects.
95 Daniel Bar-Tal, ‘The rocky road toward peace: Beliefs on conflict in Israeli textbook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5 (1998), p. 725; author interview with East Jerusalem NGO, 6 September 2013; author interview with Palestinian educator, 2 September 2013.
96 Author interview with East Jerusalem NGO, 6 September 2013; author interview with Palestinian educator, 2 September 2013.
97 Cited in Suleiman, ‘Jewish-Palestinian Relations in Israel’, p. 38.
98 Mina Cikara, Emile G. Bruneau, and Rebecca R. Saxe, ‘Us and them: Intergroup failures of empath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3 (2011),pp. 149–53; Bruneau and Saxe, ‘The power of being heard’.
99 Pfeil,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Israeli-Palestinian grassroots dialogue workshops’, p. 10.
100 Siniver, ‘Israeli Identities’, p. 38; Bar-Tal, ‘The rocky road’; Nava Sonnenschein, Zvi Bekerman, and Gabriel Horenczyk, ‘Threat and the majority identity’,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4:1 (2010), pp. 47–65.
101 Bar-Tal, ‘The rocky road’; Hammack, Narrative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